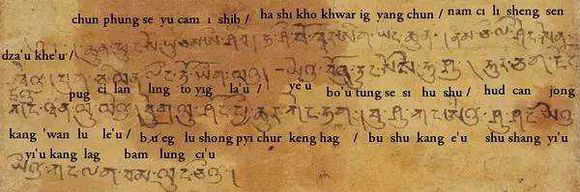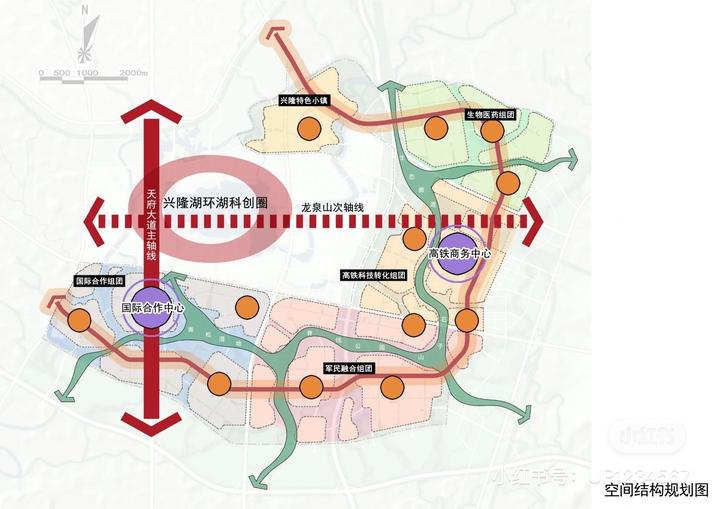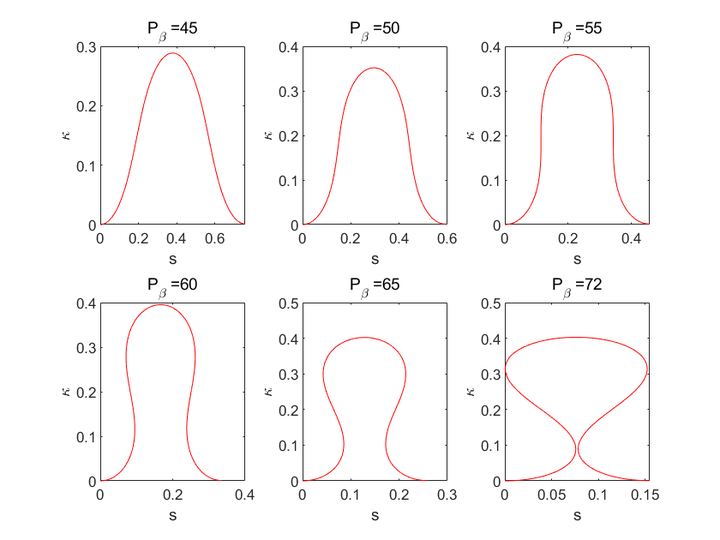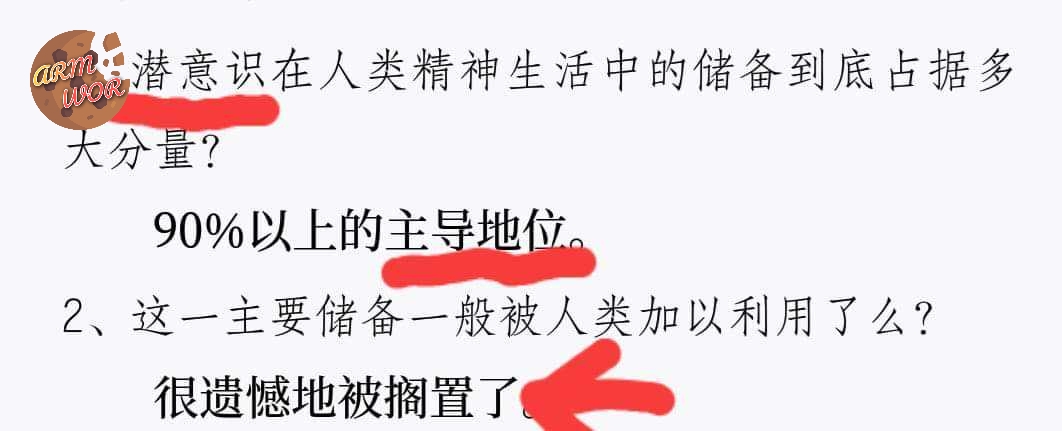日本式的“深刻”----1995版《攻壳机动队》
在《攻壳机动队》诞生之前,《银翼杀手》已经得到了声誉上的修正。从表达主题与架构方式来看,押井守似乎受到了菲利普迪克和来德利斯科特的很多启发,用一种更加“不商业”的方式,以相对严肃的姿态,重新探讨了这一主题。这让作品的剧情线索变得不那么波澜起伏,不具备太多的转折变化,甚至有些干瘪单薄。押井守将剧情用作了人物做出各种反应的引线,从而构建起了人物对内心的自我思考,以及与他人形成交互的内在表达。甚至我们可以说,《攻壳机动队》的剧情,也是为了创造一些具有主题表达作用的画面,而存在着的工具化环节。在第一部剧场版的前半部分,作品的重心放在了以下几点上:第一阶段下,接受大量改造的义体人与世界的差异化隔阂,义体人在无意识中形成对自我认知的“去人化”动摇;第二阶段里,对于义体人倾向的展示,改造更少的人类对世界的自然融入,人类与义体人的不同;第三阶段中,人类与义体人基于“内心情感”的趋同,二者无关于"身体改造比例“的精神层面共性,以情感而形成的人性本质。对第一阶段,押井守设计了几个围绕着光学迷彩的画面手法。开头的暗杀中,在人类保镖的注视之下,素子启动了光学迷彩服,逐渐进入了不可见的状态,但她身形造成的现实图景扭曲化,与周围正常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凸显出了其作为义体人,与人类世界的不融入。光学迷彩仿佛成为了区别义体人与人类的屏障,这也包括了对穿着光学迷彩服所需条件的设计-----如果是正常人类,在羞耻心之下,显然不能以裸体的姿态进行穿戴。而裸体,也成为了义体人对人类羞耻感的感受淡薄之表现,在开头的素子裸身之中,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。躯体接受改造后的去肉体化,在潜移默化中让她失去了”暴露裸体“的意识,而更接近于"展示身外之物”,由此也就淡化了作为人类理应拥有的羞耻感。素子在其后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对自身“不再是人“的迷惑,而这种心态在此处便已经得到了铺垫。根据台词,我们也看到素子对于义体化自身的安分守己:她只是完成任务,执行义体被要求的命令,而作为剧情背景的复杂国际政治,则是专属于人类的东西,与她没有关系。在领导们讨论着政治阴谋与交往权衡之时,她往往是漠然的,似乎游离于这个话题之外,只等待着具体的命令下达。这也是本片中看似复杂的政治化剧情背景,在实际应用中的最主要作用了----它当然是紧贴90年代时事的,但远远没有承载押井守的什么政治态度表达,只是为了强化片中人类世界的真实感。而当剧情来到了第二阶段,素子抓捕垃圾车的段落,除了二人隐身后的现实扭曲画面之外,押井守还加入了对远景和第一人称视角的使用。在远景中,我们看到了义体犯人站在未曾扭曲,真实感爆棚的城市背景之前的动作,他与光学迷彩中的素子战斗。在现实的大背景之下,光学迷彩造成的扭曲微不可见,这让他仿佛在与空气恶战,并被虚空地抛飞,折断手臂。于是,前景的他与后景的现实,就此隔绝开来。此外,在第一人称中,他眼中看到的远景世界,呈现了非现实感极强,属于义体人改造后视野的深蓝色。同样的第一人称视角,也出现在了素子一方的画面中。对于义体人对人类世界的距离感,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表现手段-----在他们被改造过的眼球中,世界并不是真实的颜色。而在这一阶段,义体犯人与人类也形成了内心层次上的对比:收垃圾的小哥,接受义体改造的程度更小,”人类“属性更多,他对于家庭滔滔不绝地表达着热爱,与同事之间的互动显得无比自然;而相比之下,义体犯人被小哥称为“朋友”,甚至不惜冒着被抓捕的风险,也要提前示警,他却对着小哥无情地开枪,在人情之上区别明显。义体人与人类世界的分隔,义体人与人类之于人心情感的区别,就此确立。事实上,在这一阶段,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第三阶段的影子。义体犯人跑出小巷,看着远方楼宇,上空的飞机,露出了微笑,这暗示了他对于人类世界的向往。而素子,也在第三阶段中表现出了这种向往。她在业余时间里潜水休闲,做着不符合义体人常规的事情,也对同事叙说了自己关于“有记忆就构成了完整的我”的想法。这一小段落,是对于义体人拥有人性本质的表现。押井守首次让素子脱离了义体人对应的”工作者“状态,带着她进入了休闲时间,而正如巴特所说,这本来不应该是义体人应该有的举动。脱离义体人的常规状态后,素子便回归了”人“的一面,表现出了对人类身份的回归。她的潜水,仿佛是在进入羊水,并以跃出水面的方式,让自己获得人类的”出生“。而当巴特说出义体人的记忆与肢体要归公的时候,她否定了这种将他们”工具化“的说辞,而是把工具属性更强的”虚假记忆“看作了提供真实情感,定义完整自我的人性要素。这正是她在表层迷惑之下,更加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,是对于自己人类属性的信念。在义体化的生活与工作中,这种信念会被动摇,就像她看到虚假记忆戳穿后成为”空壳“的清洁工小哥之后的反应,但不可能被彻底抹除。在说着这些的同时,素子背后的楼宇逐渐放大,与素子愈发靠近,暗示着她与人类世界的距离变化。义体人的记忆不独属于自己,随时可能归还组织,这决定了他们在人类世界中的工具化。然而,这种作为义体人活动的记忆,也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,独立思想,让他们成为了“自我”,赋予了他们作为人类的觉醒能力。押井守设计了“镜面”构图,让素子先后出现在镜中与湖里,两个素子相对而立,仿佛她作为义体人与人类的并行存在,表现出她的双重属性。另一方面,人类也呈现出了“情感决定人性”的属性。人类司机发现自己记忆的虚假,瞬间变成了空壳,周围也不再是自然的街景,而变成了灰黑的色调。而一句“当你有了感受的时候,真假就不重要了”,则是对素子等义体人之人性的肯定,让情感本身的重要性脱离了客观真假,也脱离了义体人与人类在身体机能上的肉体区别,同时拥有了人性的可能。人类想要使用义体人作为工具,因此用了植入记忆、入侵记忆的方式。然而,它带来的,必将是义体人的人性觉醒,以及相应的灾难。人类司机被植入记忆后的空壳化结果,正是前半部里对这种悲剧的铺垫。义体人对此的反抗,也正与《银翼杀手》一样。这也是作品引入国际政治背景的又一个目的----人类的阴谋,正如他们作为阴谋手段的“植入记忆,入侵躯壳”,对于义体的工具化运用,这种负面的东西并非“人”的根本,无论警察组织的正当运用,还是外国团体的非法犯罪,都是如此,“情感”才是为“人”的根本。作品的后半部分,则是对于第三阶段的加深与升级。首先,素子对于自身非人的迷惑更明显了,由清洁工小哥的空壳化而引导出来。当她扭头看向天空的时候,空中飞过了飞机,这与此前的义体罪犯高度吻合,是素子在潜水完毕、”记忆让我完整“的表达之后,另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向往,推翻了她在开篇时对于人类世界通行的羞耻感、政治外交的冷淡反应。然而,在随后的一连串镜头中,押井守却没有就此让素子回归人类,而是围绕着她绝大部分身体都改造为义体的肉体现状,强调着义体人与现实人类世界的隔阂之存在。素子坐船穿行于城市之中,然而她所在的环境,却与客观的真实世界存在着一定的区别。首先是“光学迷彩”的延伸使用,它会让城市的景象变得扭曲起来,而在这里,镜头往往让城市景色出现在水面之上,以水的波动同样扭曲了它。在给到楼宇本身的时候,押井守则保持了倾斜构图,继续强化扭曲感。相对地,在素子仰望的正常非扭曲的楼宇之中,她看到了另一个自己,穿着普通的服装,打发着闲暇的时光。在她的理解中,这正是作为“人类”---而非“义体”----的自己,已经与她本人分离开来,处在一个她只可远观而无法进入的正常世界里。同样的表达,也出现在了素子潜水的场景里。她与眼前的另一个自己近在咫尺,却无法与之融合,只会带来破水而出的幻象毁坏。在这一段的最后,押井守给出了一个与此前“素子背后的楼宇逐渐靠近”镜头相反的画面。作为纯粹生物的小猫,被平衡构图作稳定的呈现,却离镜头越来越远。这是一个隐形的素子第一人称视角,表现着她眼中自己与普通生命的渐行渐远。随之,素子身处的城市开始下雨,一切笼罩在了水面的延伸状态之下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水滴折射了光线,扭曲起来。素子望向的木头模特,巴士上的人体广告,都加深了素子的非人类认知。而在最后阶段,作品引来了一个对义体人本质属性的极致表达载体:进入女性躯壳的傀儡师。傀儡师的出场,只在镜头中露出了两条僵硬的小腿,让人想起了之前的塑料模特,眼神也显得毫无生气。在捕获它之后,警察领导等人的定性,更是明确无比:它没有自己的大脑,其GHOST---无实体的个体生命“鬼魂”----由外部入侵灌输,占据了它的躯壳,因此它只是一个他人GHOST的容器。在多方交涉的说辞中,他们直接将其中的GHOST当成了”情报“。当阴谋进一步揭开后,相关的表现变得更加丰富。警察组织内部围绕着傀儡师计划的你来我往,说明了他们对人造之物的进一步工具化意图-----不再仅仅是作品前半段中,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义体,更包括了精神层面的灵魂GHOST。在这里,作品依旧延续了其对于政治与阴谋的一贯处理方式,用语言叙述的方式给出内容,呈现了其复杂,但却并没有做太多展开,从而淡化了对阴谋本身的思考整理,而是聚焦于义体人卷入这种莫名的漩涡,被当作博弈工具的状态。此前只是略给概念的联网与ghost,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,成为了互联网世界中对“情感与记忆形成的灵魂”的指代。与之同步,义体人的极限也随之出现,将主题的探讨带入新的阶段。这个女性义体甚至没有独立的灵魂,而是由他人完全的意识占领产物,仿佛他人穿着的一件衣服,灵魂、记忆、情感,都全然不存在。素子此前对壮汉所说的迷惑,”在改造的过程中,我们是不是被植入了其他GHOST,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“,在傀儡师的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呈现---改造得最彻底,灵魂与记忆完全来自于他人,因此也就比自己产生记忆与反馈的素子等人更虚假,彻底的躯壳化让它成为了容器,在信息战等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中,也就成为了比素子等人更纯粹的工具。然而,这种极致的躯壳化,才带来了对人之本质属性的极致强调。在傀儡师看来,它没有原本的自我肉体,因此也就没有不属于自己的肉体躯壳。它的唯一自我,是携带记忆与情感的灵魂,每一具拥有灵魂的躯壳便都成为了它的”本体“。肉体的极致躯壳化与”人类定义“的关系,就此被彻底斩断了,能做出该定义的根本就不是物质,而是精神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傀儡师的”躯壳“开始说话时,它的神态也不再是此前的茫然,眼神中流露出了属于人类的一丝得意与狡黠。作为灵魂状态下的人类,反抗将自己当作工具的物质状态敌人,有着非常合理的动机。而傀儡师的反抗,升级到最终阶段后,就像他本人所说的“唯一一件还没做到的事情”,便是对于人类最独有行为-----“创造生命”----的实现。它与素子,两个义体改造程度极高的存在,以结合的方式带来一个全新的小女孩。这个设计,也对接了后半部中提出的“DNA”与“GHOST”等同之概念。GHOST在网络世界中传送,进入义体的躯壳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信息,更是对义体进行”此为何人“之定性的注入灵魂。而相对地,DNA在物质世界中传递,也并非一段遗传信息,而是将一具肉体塑造为举有独特性之存在的关键要素。DNA在广博的物质世界之中,GHOST则在同样广博的网络世界之中,让其成为了对非物质之精神世界的象征。任何人都不能将DNA当作单纯的信息工具,也就不能那样看待GHOST。互联网不具有实体的”非现实“之虚构性,暗合着义体人在物质层面上的肉体不纯粹,而”互联网DNA“GHOST的存在,便也让义体人肉体上的改造不再成为对其生命定义的阻碍,哪怕其在物质层面上确实是非自然的”人造物“。对于“人性根本的去物质化“,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有着更细致的体现。一方,是被组织命令着的屠杀机器,在数个数码状态的摄影机主观视角里,进行着索敌。而另一方,则是自主行动的素子。在物质层面极端工具化,却在精神层面极致人性化的傀儡师的影响之下,素子接收到了他最坚定的自我信念,从而摆脱了自己的迷惑和摇摆,完成了对“人”的回归。在打斗中,素子的义体被机器毁坏,变得破破烂烂,随后出现了火力破坏生物树的特写,对这一段下了定义:组织试图用抹杀物质躯体的方式,消灭素子和傀儡师的生命,根除拥有自由向往、不再听从自己命令与计划的造物,而他们的理想造物,正是屠杀机器那样完全不具备自主意识的东西,其理想初衷便带有强烈的生命抹除意味。然而,素子和傀
在《攻壳机动队》诞生之前,《银翼杀手》已经得到了声誉上的修正。从表达主题与架构方式来看,押井守似乎受到了菲利普迪克和来德利斯科特的很多启发,用一种更加“不商业”的方式,以相对严肃的姿态,重新探讨了这一主题。这让作品的剧情线索变得不那么波澜起伏,不具备太多的转折变化,甚至有些干瘪单薄。押井守将剧情用作了人物做出各种反应的引线,从而构建起了人物对内心的自我思考,以及与他人形成交互的内在表达。甚至我们可以说,《攻壳机动队》的剧情,也是为了创造一些具有主题表达作用的画面,而存在着的工具化环节。
在第一部剧场版的前半部分,作品的重心放在了以下几点上:第一阶段下,接受大量改造的义体人与世界的差异化隔阂,义体人在无意识中形成对自我认知的“去人化”动摇;第二阶段里,对于义体人倾向的展示,改造更少的人类对世界的自然融入,人类与义体人的不同;第三阶段中,人类与义体人基于“内心情感”的趋同,二者无关于"身体改造比例“的精神层面共性,以情感而形成的人性本质。
对第一阶段,押井守设计了几个围绕着光学迷彩的画面手法。开头的暗杀中,在人类保镖的注视之下,素子启动了光学迷彩服,逐渐进入了不可见的状态,但她身形造成的现实图景扭曲化,与周围正常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凸显出了其作为义体人,与人类世界的不融入。光学迷彩仿佛成为了区别义体人与人类的屏障,这也包括了对穿着光学迷彩服所需条件的设计-----如果是正常人类,在羞耻心之下,显然不能以裸体的姿态进行穿戴。而裸体,也成为了义体人对人类羞耻感的感受淡薄之表现,在开头的素子裸身之中,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。躯体接受改造后的去肉体化,在潜移默化中让她失去了”暴露裸体“的意识,而更接近于"展示身外之物”,由此也就淡化了作为人类理应拥有的羞耻感。素子在其后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对自身“不再是人“的迷惑,而这种心态在此处便已经得到了铺垫。
根据台词,我们也看到素子对于义体化自身的安分守己:她只是完成任务,执行义体被要求的命令,而作为剧情背景的复杂国际政治,则是专属于人类的东西,与她没有关系。在领导们讨论着政治阴谋与交往权衡之时,她往往是漠然的,似乎游离于这个话题之外,只等待着具体的命令下达。这也是本片中看似复杂的政治化剧情背景,在实际应用中的最主要作用了----它当然是紧贴90年代时事的,但远远没有承载押井守的什么政治态度表达,只是为了强化片中人类世界的真实感。
而当剧情来到了第二阶段,素子抓捕垃圾车的段落,除了二人隐身后的现实扭曲画面之外,押井守还加入了对远景和第一人称视角的使用。在远景中,我们看到了义体犯人站在未曾扭曲,真实感爆棚的城市背景之前的动作,他与光学迷彩中的素子战斗。在现实的大背景之下,光学迷彩造成的扭曲微不可见,这让他仿佛在与空气恶战,并被虚空地抛飞,折断手臂。于是,前景的他与后景的现实,就此隔绝开来。此外,在第一人称中,他眼中看到的远景世界,呈现了非现实感极强,属于义体人改造后视野的深蓝色。同样的第一人称视角,也出现在了素子一方的画面中。对于义体人对人类世界的距离感,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表现手段-----在他们被改造过的眼球中,世界并不是真实的颜色。
而在这一阶段,义体犯人与人类也形成了内心层次上的对比:收垃圾的小哥,接受义体改造的程度更小,”人类“属性更多,他对于家庭滔滔不绝地表达着热爱,与同事之间的互动显得无比自然;而相比之下,义体犯人被小哥称为“朋友”,甚至不惜冒着被抓捕的风险,也要提前示警,他却对着小哥无情地开枪,在人情之上区别明显。义体人与人类世界的分隔,义体人与人类之于人心情感的区别,就此确立。
事实上,在这一阶段,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第三阶段的影子。义体犯人跑出小巷,看着远方楼宇,上空的飞机,露出了微笑,这暗示了他对于人类世界的向往。而素子,也在第三阶段中表现出了这种向往。她在业余时间里潜水休闲,做着不符合义体人常规的事情,也对同事叙说了自己关于“有记忆就构成了完整的我”的想法。这一小段落,是对于义体人拥有人性本质的表现。押井守首次让素子脱离了义体人对应的”工作者“状态,带着她进入了休闲时间,而正如巴特所说,这本来不应该是义体人应该有的举动。脱离义体人的常规状态后,素子便回归了”人“的一面,表现出了对人类身份的回归。她的潜水,仿佛是在进入羊水,并以跃出水面的方式,让自己获得人类的”出生“。而当巴特说出义体人的记忆与肢体要归公的时候,她否定了这种将他们”工具化“的说辞,而是把工具属性更强的”虚假记忆“看作了提供真实情感,定义完整自我的人性要素。这正是她在表层迷惑之下,更加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,是对于自己人类属性的信念。在义体化的生活与工作中,这种信念会被动摇,就像她看到虚假记忆戳穿后成为”空壳“的清洁工小哥之后的反应,但不可能被彻底抹除。在说着这些的同时,素子背后的楼宇逐渐放大,与素子愈发靠近,暗示着她与人类世界的距离变化。
义体人的记忆不独属于自己,随时可能归还组织,这决定了他们在人类世界中的工具化。然而,这种作为义体人活动的记忆,也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,独立思想,让他们成为了“自我”,赋予了他们作为人类的觉醒能力。押井守设计了“镜面”构图,让素子先后出现在镜中与湖里,两个素子相对而立,仿佛她作为义体人与人类的并行存在,表现出她的双重属性。另一方面,人类也呈现出了“情感决定人性”的属性。人类司机发现自己记忆的虚假,瞬间变成了空壳,周围也不再是自然的街景,而变成了灰黑的色调。而一句“当你有了感受的时候,真假就不重要了”,则是对素子等义体人之人性的肯定,让情感本身的重要性脱离了客观真假,也脱离了义体人与人类在身体机能上的肉体区别,同时拥有了人性的可能。
人类想要使用义体人作为工具,因此用了植入记忆、入侵记忆的方式。然而,它带来的,必将是义体人的人性觉醒,以及相应的灾难。人类司机被植入记忆后的空壳化结果,正是前半部里对这种悲剧的铺垫。义体人对此的反抗,也正与《银翼杀手》一样。这也是作品引入国际政治背景的又一个目的----人类的阴谋,正如他们作为阴谋手段的“植入记忆,入侵躯壳”,对于义体的工具化运用,这种负面的东西并非“人”的根本,无论警察组织的正当运用,还是外国团体的非法犯罪,都是如此,“情感”才是为“人”的根本。
作品的后半部分,则是对于第三阶段的加深与升级。首先,素子对于自身非人的迷惑更明显了,由清洁工小哥的空壳化而引导出来。当她扭头看向天空的时候,空中飞过了飞机,这与此前的义体罪犯高度吻合,是素子在潜水完毕、”记忆让我完整“的表达之后,另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向往,推翻了她在开篇时对于人类世界通行的羞耻感、政治外交的冷淡反应。然而,在随后的一连串镜头中,押井守却没有就此让素子回归人类,而是围绕着她绝大部分身体都改造为义体的肉体现状,强调着义体人与现实人类世界的隔阂之存在。素子坐船穿行于城市之中,然而她所在的环境,却与客观的真实世界存在着一定的区别。首先是“光学迷彩”的延伸使用,它会让城市的景象变得扭曲起来,而在这里,镜头往往让城市景色出现在水面之上,以水的波动同样扭曲了它。在给到楼宇本身的时候,押井守则保持了倾斜构图,继续强化扭曲感。
相对地,在素子仰望的正常非扭曲的楼宇之中,她看到了另一个自己,穿着普通的服装,打发着闲暇的时光。在她的理解中,这正是作为“人类”---而非“义体”----的自己,已经与她本人分离开来,处在一个她只可远观而无法进入的正常世界里。同样的表达,也出现在了素子潜水的场景里。她与眼前的另一个自己近在咫尺,却无法与之融合,只会带来破水而出的幻象毁坏。在这一段的最后,押井守给出了一个与此前“素子背后的楼宇逐渐靠近”镜头相反的画面。作为纯粹生物的小猫,被平衡构图作稳定的呈现,却离镜头越来越远。这是一个隐形的素子第一人称视角,表现着她眼中自己与普通生命的渐行渐远。随之,素子身处的城市开始下雨,一切笼罩在了水面的延伸状态之下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水滴折射了光线,扭曲起来。素子望向的木头模特,巴士上的人体广告,都加深了素子的非人类认知。
而在最后阶段,作品引来了一个对义体人本质属性的极致表达载体:进入女性躯壳的傀儡师。傀儡师的出场,只在镜头中露出了两条僵硬的小腿,让人想起了之前的塑料模特,眼神也显得毫无生气。在捕获它之后,警察领导等人的定性,更是明确无比:它没有自己的大脑,其GHOST---无实体的个体生命“鬼魂”----由外部入侵灌输,占据了它的躯壳,因此它只是一个他人GHOST的容器。在多方交涉的说辞中,他们直接将其中的GHOST当成了”情报“。当阴谋进一步揭开后,相关的表现变得更加丰富。警察组织内部围绕着傀儡师计划的你来我往,说明了他们对人造之物的进一步工具化意图-----不再仅仅是作品前半段中,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义体,更包括了精神层面的灵魂GHOST。在这里,作品依旧延续了其对于政治与阴谋的一贯处理方式,用语言叙述的方式给出内容,呈现了其复杂,但却并没有做太多展开,从而淡化了对阴谋本身的思考整理,而是聚焦于义体人卷入这种莫名的漩涡,被当作博弈工具的状态。
此前只是略给概念的联网与ghost,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,成为了互联网世界中对“情感与记忆形成的灵魂”的指代。与之同步,义体人的极限也随之出现,将主题的探讨带入新的阶段。这个女性义体甚至没有独立的灵魂,而是由他人完全的意识占领产物,仿佛他人穿着的一件衣服,灵魂、记忆、情感,都全然不存在。素子此前对壮汉所说的迷惑,”在改造的过程中,我们是不是被植入了其他GHOST,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“,在傀儡师的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呈现---改造得最彻底,灵魂与记忆完全来自于他人,因此也就比自己产生记忆与反馈的素子等人更虚假,彻底的躯壳化让它成为了容器,在信息战等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中,也就成为了比素子等人更纯粹的工具。
然而,这种极致的躯壳化,才带来了对人之本质属性的极致强调。在傀儡师看来,它没有原本的自我肉体,因此也就没有不属于自己的肉体躯壳。它的唯一自我,是携带记忆与情感的灵魂,每一具拥有灵魂的躯壳便都成为了它的”本体“。肉体的极致躯壳化与”人类定义“的关系,就此被彻底斩断了,能做出该定义的根本就不是物质,而是精神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傀儡师的”躯壳“开始说话时,它的神态也不再是此前的茫然,眼神中流露出了属于人类的一丝得意与狡黠。作为灵魂状态下的人类,反抗将自己当作工具的物质状态敌人,有着非常合理的动机。
而傀儡师的反抗,升级到最终阶段后,就像他本人所说的“唯一一件还没做到的事情”,便是对于人类最独有行为-----“创造生命”----的实现。它与素子,两个义体改造程度极高的存在,以结合的方式带来一个全新的小女孩。这个设计,也对接了后半部中提出的“DNA”与“GHOST”等同之概念。GHOST在网络世界中传送,进入义体的躯壳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信息,更是对义体进行”此为何人“之定性的注入灵魂。而相对地,DNA在物质世界中传递,也并非一段遗传信息,而是将一具肉体塑造为举有独特性之存在的关键要素。DNA在广博的物质世界之中,GHOST则在同样广博的网络世界之中,让其成为了对非物质之精神世界的象征。任何人都不能将DNA当作单纯的信息工具,也就不能那样看待GHOST。互联网不具有实体的”非现实“之虚构性,暗合着义体人在物质层面上的肉体不纯粹,而”互联网DNA“GHOST的存在,便也让义体人肉体上的改造不再成为对其生命定义的阻碍,哪怕其在物质层面上确实是非自然的”人造物“。
对于“人性根本的去物质化“,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有着更细致的体现。一方,是被组织命令着的屠杀机器,在数个数码状态的摄影机主观视角里,进行着索敌。而另一方,则是自主行动的素子。在物质层面极端工具化,却在精神层面极致人性化的傀儡师的影响之下,素子接收到了他最坚定的自我信念,从而摆脱了自己的迷惑和摇摆,完成了对“人”的回归。
在打斗中,素子的义体被机器毁坏,变得破破烂烂,随后出现了火力破坏生物树的特写,对这一段下了定义:组织试图用抹杀物质躯体的方式,消灭素子和傀儡师的生命,根除拥有自由向往、不再听从自己命令与计划的造物,而他们的理想造物,正是屠杀机器那样完全不具备自主意识的东西,其理想初衷便带有强烈的生命抹除意味。然而,素子和傀儡师可以被毁去躯体,但他们的灵魂却完成了创造生命的融合,并以新生命的形式独立地长存于互联网世界。互联网意味着精神意识的世界,这才是人性的根本所在,躯壳是可以被舍弃的。就像在战斗中,素子的躯体被破坏,但古塔萨依然会在左轮手枪无用之后,想起片头素子对此的吐槽而会心一笑,显示出素子与旁人始终存在的情感交织。
因此,由于义体人拥有GHOST,他们也就成为了电线连接起的网络世界里的生命,具有了创造生命的能力。新生命的小女孩出生,她看向世界,对巴特说出了“我不再是傀儡师,也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素子少佐”,说明了她的独立性质----这是一个全新的灵魂,而非傀儡师和素子的精神进入的另一躯壳,这正是“孕育生命”的表现。在物质层面,她只是巴特捡来的一个女孩义体,并不具备独特性。但在更加根本的精神层面上,她成为了完全的生命体ghost,去往了非物质,却又远非虚构人性的生命本质世界---对应精神空间的互联网空间。在最后一组镜头中,显示屏一样的主观视角,拥有噪点的房间,噪点消失的房间,先后出现,意味着义体人世界的逐渐真实化。而在最后,小女孩看向远方的世界,说出了“互联网如此广博”,更是彻底将互联网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看作了等同的东西。这推翻了通篇保持的义体人世界处理方式,推翻了显示器与摄影机化的视角,三维成像后的街头画面,以及雨水折射中的楼宇巷弄,完全肯定了精神世界与其中生命的真实存在,让它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再无任何不同。
DNA与GHOST的等同,是本片中相当大的一个亮点。它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90-00年代相吻合,借着非现实的互联网世界,让片中关于”生命定义“的表现方式变得更加具象,更可触及了一些。在后作《无罪》中,它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延展使用。
在一定程度上,这中和了作品的一些不足之处。相比于更加大部头的同类型电影作品,它的人物虽然在迷惑,虽然由此生出了复杂的心理状态,但更多地停留在了对人物对自己属性的”迷惑“本身,对其情绪的呈现之上。角色用台词诉说着迷惑相关的不同心理层次,押井守则用镜头语言传达着同样的内容。然而,文本层面却暴露了一定的缺失,并没能承接上相应的深度,人物对于自我存在的迷惑也就没有作用、反应于更细化的具体行为、思维逻辑之上。这个缺失,让作品的思辨更多是在”自我认知“本身的角度上,而没有”具体为何有这种认知,这种认知带来了什么“。或许,所谓的”晦涩“,也多少是由于,”更容易理解“的文本有所缺失,而以更不直接的表达方式取而代之了。
事实上,这一点,可谓是日式”深度“作品的一种”特色“了。无论是《赛博朋克边缘跑者》这样的欧美发行+日本创作,还是日式RPG的游戏作品,它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设立一个纵向上非常”深度“的立意主题,然后在横向的延展扩充环节则有所不足。起调够深,而挖掘,却未必同样地那么深。
这可以是主题表达角度上的“不足”。当然,它也同样可以是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都难以完美创造出的个性腔调,是一种“特色”。与其说是挖掘的“深度”,向纵深而去的思考剖析,它更突出的,似乎是设题的“高度”,以及对这一高度上风景的展示。
来源:知乎 www.zhihu.com
作者:segelas
【知乎日报】千万用户的选择,做朋友圈里的新鲜事分享大牛。
点击下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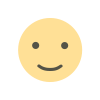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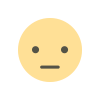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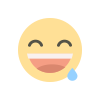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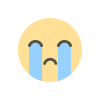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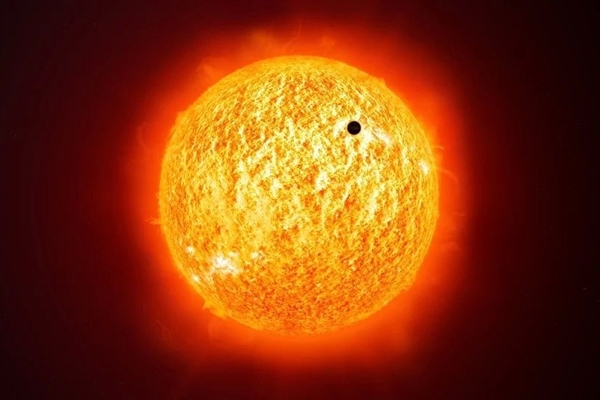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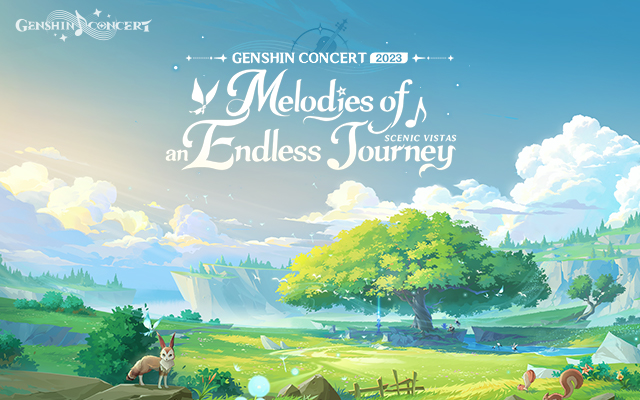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![【XGAMER 元代碼 - 主題曲: 寂聲 (日本語)】 日語歌詞: Verse 1 目を閉じたいだけ 気にしていないふうに... 内の信念は 正しくない 風と海[真実を]告げて 失くしない 幻がなくて Chorus: 徹夜で戦った 日差し...](https://scontent.fdsa2-1.fna.fbcdn.net/v/t15.5256-10/336656091_162215126698640_3843734250325810940_n.jpg?stp=dst-jpg_p600x600&_nc_cat=102&ccb=1-7&_nc_sid=08861d&_nc_ohc=kQATFNXRo-kAX9EeaEw&_nc_ht=scontent.fdsa2-1.fna&oh=00_AfCnUOW2Bv6j_cgJTtG7RU2CcjvsthXu1Pj6XjGBE5943w&oe=641C69A7#)